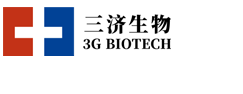前不久,我和威廉姆·法尔医生(William Fair)在他上东区的办公室见了面,他刚刚看完病人,脱下白大褂,坐在高背真皮转椅上。“医生认为我的结肠癌是不治之症,所以我想给自己当一回医生。”法尔医生这么告诉我。他光亮的橡木书桌上杂乱地放着着各种文件,书架上塞满了各种医学期刊。
威廉姆·法尔医生(William Fair)
尽管这样,法尔看起来很宁静淡泊,但稍显刻意,就像退休后开始伺弄花草的高官一样。他现年63岁,淡金发色,脸色红润,碧眼澄澈,以他的年纪来看算是保养得很好。谈到自己的病情时,法尔常常面带微笑似乎是想让他的访客放松。然而根据他同事谨慎礼貌的评论,你可以推测出他曾经是什么样的人:难以驾驭、神经紧张、专横傲慢、缺乏耐心。一言以蔽之,他拥有一流外科医生的所有性格特征:认为做了总比没做好。
最近,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他决定停止过去的常规疗法。大部分癌症疗法都是“万金油”疗法:待选药物首先会在试管中通过原型肿瘤进行筛选,然后在一些无法治愈的病人身上进行随机的临床测试。法尔医生已经加入到“不能治愈”患者之列。他坚信只有在实验室里研究自己的肿瘤,致力于寻找为他自身癌症量身定做的特异疗法,他才有可能真正被治愈。目前为止,结果都还是让人乐观的。
初患癌症:无畏无惧
从1984年到1997,威廉姆·法尔医生在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担任了13年的泌尿科主任,该癌症中心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癌症医院。法尔医生是一位杰出的外科医生,专门从事前列腺癌、膀胱癌、睾丸癌以及肾脏癌的研究。他一天内可以进行五次手术,指导肿瘤外科的研究项目,参加部门里的所有行政棘手事宜——决定人事变动、裁定地盘斗争,商议工资浮动等。
“我有外科医生典型的超人情结,所以忽略了初期的症状,”法尔在叙述自己的病史时说。199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常感到疲惫、心悸、晕眩。尽管疲惫不堪,他依然坚持高强度的工作日程——手术、研究以及行政管理。“他就是那种一天工作24小时,一周工作7天的工作狂。”斯科普·赫斯顿医生(Dr. Skip Heston)说,他是泌尿科的首席实验科学家,与法尔共事了25年,“我不喜欢那一年法尔的状态。”
法尔的妻子也有同感,她曾是一名军队护士。她没有与法尔商议,直接帮他预约了一位内科医生。法尔知道后,取消了预约:因为他没有时间。最后,法尔的妻子和赫斯顿说服他进行了体检。结果发现他有严重的贫血症——他结肠里的肿瘤会渗血。
“如果你得了癌症,”法尔医生说,“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只字不提,要么放开了谈。”他向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全体员工告知了他的病情,他们马上集中力量,提供帮助。他在自己的医院就可以得到最好的治疗。尽管如此,这位外科医生可没有那么容易放弃他的职权。1995年1月,法尔躺在轮床上被推向一间手术室,在手术室里,认出了躺在另一辆轮床上的患者。之前法尔医生安排当天上午给这位患者进行手术,法尔用一只手的肘部撑起身体,向病人保证他已经安排好了一切——他安排了一位优秀的医生代替他而且一切尽在掌控中。
结肠直肠科的首席外科医生给法尔做了手术,其接受手术有两个目标:切除肿瘤,以及用外科方法探索感染部位。如果肿瘤被证实只存在于肠道中,并没有扩散到腹部邻近的淋巴结或者其他部位的话,此次手术应该能达到疗效的目标。不幸的是,肿瘤附近的两个淋巴结中存在扩散了的肿瘤沉淀物。
威廉姆·法尔被这个消息震惊了。他能再活5年的几率是40%。他明白,如果淋巴结里有肿瘤,那么周围往往会有其它的肿瘤沉淀物,而且沉淀物太小了,最好的外科大夫都很难发现并切除。法尔医生也清楚结肠癌对放疗和化疗尤其有抵抗力。在这种情况下,专门从事研究肠道癌研究的肿瘤学家戴维·凯尔森医生(Dr. David Kelsen)推荐了一种辅助化疗。其作用机制是:大块肿瘤切除后,剩余的肿瘤体积小,在这种状况下,毒性药物能更好的发挥疗效。但是辅助化疗方法最多只能将法尔医生的存活率提高到50%。
药物直接输注到腹腔的疗法持续了3个月,之后他又接受了12个月的静脉内化疗。在治疗期间,法尔坚持给患者做手术,他说,“我会做3到4个小时的手术,结束之后就跑着赶去化疗,随后又赶回来做下一个手术,”法尔的儿子威廉姆三世,经营着一家医疗保健公司。他回忆起,1996年法尔医生完成了化疗之后,坚持要在儿子十六岁生日时到加拉帕戈斯群岛度一个两周的假。“他当时非常虚弱,去的时候还带上了静脉注射液和药,以此支撑自己。尽管如此,他还是跑到了导游前面,跳进一个皮划艇,独自划走了。”
法尔医生告诉自己,他的人生会回到过去三十年的轨道的。在接受治疗一年之后,他的话似乎灵验了,简直就像他用意念控制的一样。随后,在1997年1月,一项常规后续CAT扫描显示,他的肝脏旁边的一个淋巴结里长了一个大块的肿瘤。
首次复发:治疗该何去何从
法尔回忆起当时“精神崩溃”的情形。他能活5年的的几率骤降至1/10,当时可行的疗法中没有一种是特别有可能治愈法尔的结肠癌。由于化疗和放疗具有毒性且效果有限,也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数据表明这样的治疗可以延长法尔的生命,他选择了姑息性手术。法尔医生体内的肿瘤团块将会被剪除,并不是期望借此根除癌症,而是希望能够减缓癌症恶化的进程。
畏缩不前并不是法尔医生的做事风格,他的家人清楚地记得他们在坦桑尼亚的旅途中遭遇了车祸,法尔医生的妻子腿部受伤严重,法尔医生不顾自己肋骨和手腕的骨折,果断地帮妻子止血,用随身携带的瑞士军刀和一些缝合材料帮妻子缝合伤口。然而,在纽约斯隆-凯特林(Memorial Sloan-Kettering)癌症研究中心的咨询室里,法尔医生却被告知药物干预的标准疗法已经穷途末路。最明智的选择就是等待,除此之外无计可施。
就在此刻,斯科普·赫斯顿医生决定在法尔医生的肿瘤上取样。“当时的想法就是要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疗法,”高大健硕,一头棕发的赫斯顿医生说道,“每个人的肿瘤都有特异性,所以我们需要亲自动手研究比尔(法尔医生)的肿瘤。”赫斯顿医生在外科手术室等候,并准备护送一片从法尔医生肝脏底部取下来的肿瘤组织。困难才刚刚开始。
肿瘤的样品被小心翼翼地转移到一个密闭的、无菌的容器中,并送到邻近的洛克菲勒研究中心(Rockefeller Research Building)4楼。如果样本途中被四处飘浮的细菌污染,癌细胞可能会死亡。在体内看似无坚不摧的癌细胞在实验室里就像脆弱的温室花朵:它们必须被滋养、保护和呵护。因此研究人员需在一个名为层流罩的无菌容器中操作。法尔的癌细胞样本被分散开,癌细胞被放置在培养皿中,其内装着类似血浆的液体,含有细胞生长所需的营养物质和激素。接着,培养皿被转移到一个恒温箱内,箱内温度与人体温度相当,且充斥着与人体血液比例相等的氧气、氮气和二氧化碳潮湿气体混合物。很快,癌细胞开始增殖。第一个障碍被克服。研究人员获得了足够的癌细胞来进行分类和研究。接下来赫斯顿医生和他的同事即将开始一场对抗法尔医生癌症的斗争。
癌症并不是单一的存在,而是有多种多样的变体。“癌症”不是用来命名一种疾病或者一种类型的细胞,而是成百上千种疾病和细胞的总称。即使某种特定类型癌症,例如乳腺癌、肺癌或结肠癌,每个患者的癌细胞也是独一无二的。每个肿瘤都是病人在特定环境下病变基因的错误表达。而这种病变基因的异常表达决定了肿瘤的发展:保持一个团块的形态缓慢生长,还是飞速扩散;癌细胞在放疗和化疗后会死去,还是顽强存留?
虽然癌症是多种多样并且因人而异,但是当前的癌症疗法却趋于标准化,很少注重每个病人特定肿瘤的独特特征。很大程度上而言,这些标准疗法就像是地毯式轰炸:有时候击中目标,但往往会错过目标,因为癌细胞进行了完善的自我保护应对袭击。除此之外,几乎在所有病例中,这些标准疗法都附带伤害到正常组织。法尔需要的是智能疗法,而这首先要对肿瘤的本质有更深刻的了解。在4楼的实验室里,赫斯顿医生从培养皿中收集了足量的癌细胞,并进行分析癌细胞的变异基因。他发现了名为p53的特定变异。正常情况下,p53基因限制细胞分裂,一旦发生变异细胞就会肆意生长,换句话说,癌症出现了。
你不能从囚禁的野生动物身上推断其在野生环境中的行为,同理,在培养皿中也很难检测出抗癌药物的疗效。你想更好的了解癌细胞的真正弱点就必须将它们植入动物体内生长。于是赫斯顿医生将法尔医生的癌细胞注入到有免疫缺陷的小鼠体内,如此一来,外来癌细胞就可以在它们体内生长(具有正常免疫能力的老鼠会排斥人体细胞)。截止去年夏天,赫斯顿医生的研究跨越了第二个里程碑。赫斯顿医生和同事成功培养出了一批携带法尔医生癌细胞的小鼠,于是他们便可以在小鼠身上测试新疗法。
1997年春天,威廉姆斯·法尔最终决定辞去纪念斯隆-凯特林(Memorial Sloan-Kettering)癌症研究中心泌尿科主任的职位。虽然他继续留在研究中心工作,但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有效疗法的研究中。当赫斯顿医生在实验鼠上进行试验时,法尔决定对所有可能治愈他的癌症的疗法都保持开放的心态,包括他曾经否定过的新世纪方法(New Agey)。(法尔医生的儿子回忆起法尔从前曾称新世纪方法(New Agey)就是“扯淡”)。“许多同事都觉得我是怪胎,”法尔医生冷静地说道,并描述了过去一年半来他每天接受的常规治疗计划,服用的维他命,和高蛋白、低脂肪的饮食。
对法尔医生来说,“放松自己”是一件难事,现在依旧如此。“我曾经在加利福尼亚州报名参加了减压课程,”他告诉我,“然而我每次都熬夜到眼睛布满血丝,以保证不耽误任何工作。”与许多非传统医学的狂热分子不同的是,法尔医生从未放弃对这些新医疗技术的理性评估,他的期望值是保守的。“我从来不糊弄我自己,”法尔医生说道。“我知道这些新疗法在延伸我人生的宽度,但是它们并不一定能延长我的生命。”法尔医生的经历甚至影响了他与病人的沟通方式——他现在更多的强调病人的身体状况。“从前作为一名医生的他往往会比别人思考更多,但他认为所有的事情就是非赢即输,”法尔医生的儿子告诉我,“现在我觉得他已经意识到即使无法完全治好病人,他也可以帮助他们。”
再次复发:摒弃传统疗法,探索新疗法
1997年8月初,法尔医生得到了一则更令人崩溃的消息,CAT扫描(计算机化X 射线轴向分层造影扫描)显示在他肝脏附近的淋巴结里出现了一个新的肿瘤。虽然法尔医生早已料到癌症会复发,但没想到会来的这么快。法尔医生做完姑息手术仅8个月肿瘤便再次出现,这表明他的肿瘤特别具有攻击性。为了减缓法尔医生癌症的恶化进程,同事向他推荐了一种毒性化疗药物CPT-11,法尔医生对此拿不定主意。CPT-11跟一般化疗药物的开发研究并无差异:先在试管中通过原型癌细胞进行筛选,然后在晚期癌症病人身上进行临床试验。通过CPT-11药物显著地缩小法尔医生的肿瘤的几率甚微,更不可能从真正意义上根除癌症。“当你只有一把锤子的时候,任何东西看起来都像钉子。”法尔医生总结道。他觉得必须要另辟蹊径,用于试验的小鼠已准备就绪,只欠可供试验的疗法和药物。
法尔医生提出要测试两种药物,一种追溯到过去,而另一种延伸至未来。第一种药剂是一种中草药,被包装并命名为“SPES”(治疗前列腺癌的中草药);第二种是肿瘤疫苗。两种药剂的研究准备工作都通过理性的选择,将采用赫斯顿博士在培养皿和实验鼠身上培育的癌细胞。两种药剂都代表着会对当代医药学产生巨大影响的发展趋势。
不难想象过去的法尔医生会对草药治癌的想法有怎样的反应:“扯淡!”非传统医学一般都是“长于蓝图,短于实践”——这是江湖医生拿来哄骗病入膏肓的患者的伪医术。但与此同时,这些延续了3000年的亚洲经验医术却不容忽视。再者,癌症治疗中的重要药物都源自植物:治疗乳腺癌和卵巢癌的紫杉酚是从太平洋紫杉树的针叶中提取出来的;治疗淋巴癌和白血病的长春新碱则提取于长春花植株。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民间常用紫色毛地黄缓解水肿,受此启发毛地黄对心力衰竭的医学作用才得以被认知;祖传土方中常用金鸡纳皮治疗疟疾,美国医药公司参考此法引导了金鸡纳碱和金鸡纳霜治疗疟疾的氯喹药物。
最近,大型生物制药公司都在积极从外来的自然资源中提取新药物。默克(Merck)制药公司基础研究部门的高级副主管罗杰·珀尔马特博士(Dr. Roger Perlmutter),负责监督多个项目的取样工作,取样对象包括纳米比亚长颈鹿的粪便、冰岛的间歇泉、汤加的植物以及关岛的沙蚕。这些纯天然的产物需要通过高强度的酶筛查,以试图识别其中新的抗菌、抗炎和抗癌混合物。
索菲·陈博士(Sophie Chen)是一名生物学家,她也曾在默克(Merck)制药公司做过相同的研究,现为纽约医科大学的教授。1997年9月,威廉姆斯·法尔第一次见到索菲·陈博士,当时他们都参加了在美国太皓湖由CaP CURE赞助的会议(CaP CURE是迈克尔·米尔肯成立的致力于对抗前列腺癌的慈善组织)。法尔是前列腺癌研究的权威代表,他向索菲·陈博士介绍了新的疗法。而索菲·陈博士则向法尔介绍了她与上海医科大学王旭辉博士共同进行的研究工作。
王博士的曾祖父是末代皇帝的朝廷御医,继承了历经中国政治和文化动荡考验的知识与实践体系。王博士和陈博士正在研究一种治疗前列腺癌的草本药剂,叫PC-SPES。陈博士发现这种药物能够抑制前列腺癌肿的特定变异基因,从而加速这些生存期过长细胞的死亡。这种药物包含一种与人体激素相似的物质,但同时也含有大量与染料木碱类似的物质——染料木碱能够抑制几种促癌酶的合成。法尔医生随后告知陈博士他自己的情况,并询问是否有草药的疗法可能对他的结肠癌有帮助。陈博士随后帮法尔医生联系了王博士。
法尔医生回忆道:“王医生问我,‘你的癌细胞中是否有p53基因突变’。”之后他为法尔提供了SPES制剂的原液,王博士相信该治疗方案能有效抑制带有p53基因突变的肿瘤。法尔说当时自己对此疗法持怀疑态度:“这种草药饮剂的某些说明声称能包治百病,无禁忌人群。”不过,法尔觉得病情已经到这份上了,自己也不会有什么损失,而且陈医生严谨的科学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决定进行此次试验。
赫斯顿医生准备了两组小鼠进行试验: 他在一组小鼠的日常饮食中添加了SPES的提取液,该组小鼠不但体内携带法尔医生的结肠癌细胞而且有免疫缺失障碍;另一组携带肿瘤的小鼠则喂食常规食物,作为对照组。短短几周内,喂食SPES提取液的小鼠的肿瘤缩小了50%,而对照组小鼠的肿瘤继续生长。去年9月,法尔医生得知试验结果后,便开始大量服用SPES草药,此举仅有的副作用就是腹泻。之后他将剂量调整到自己能忍受的程度,12个月后,他仍然坚持每天服用SPES。
求助好友:研发个性化癌症疫苗
研制疫苗的想法可能不如中国草药学历史久远。不过,虽然癌症疫苗听起来富有强烈的未来主义色彩,但对它的探索其实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实际上,一百多年前小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支持建立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治疗中心前身,其部分目的就是研发强化免疫系统的疫苗,以检测特异外来蛋白质,从而标靶与该蛋白质相关联的入侵微生物。然而癌细胞同样也会被癌细胞的突变基因生成的外来蛋白质打上标记,让人困惑的是机体既不会把癌细胞当做异常细胞也不会调动杀伤T细胞破坏它们。癌细胞莫名其妙地顺利规避或中断了这种反应,使得机体无法生成抵抗癌症的免疫力。有效的肿瘤疫苗能训练杀伤T细胞识别癌细胞,然后像清理细菌一样,将癌细胞清除。
斯坦福大学的罗纳尔德·赖威医生( Dr. Ronald Levy)在研发第一代抗癌疫苗上取得了一些成就。他一直崇尚个性化制定癌症治疗方案的想法,而且深知实现其追求所面临的科学难题和社会压力。赖威医生是一名淋巴瘤专家,他辨别出每位淋巴瘤患者的肿瘤中都有一种名为个体基因型免疫球蛋白的独特信号蛋白。如果可以训练病人的免疫系统识别这种蛋白质,便可引导机体的自身修复功能对抗疾病。
赖威医生回忆起17年前接诊的首位患者说道:“他的一只脚已经踏进坟墓里了。”该患者的淋巴瘤已长成肉眼可见的的团状,其不仅出现在内脏器官,连皮肤上也出现了小瘤。赖威医生从患者的癌组织中提取了淋巴瘤信号蛋白并将其移植到小鼠体内;小鼠分泌出抑制该蛋白的抗体。现在赖威医生已基本判定出哪种抗体的功能最强大,将此种抗体大量生产,并将病人肿瘤提取物注入这种特定抗体中,结果显示没有肿瘤生成。
这一令人震惊的试验结果促成了1986年赖威医生与加利福尼亚州一家名为IDEC的生物制药公司合作,共同成立了一个重要的科研项目。50名患者接受了癌症个性化治疗,值得一提的是为期6个多星期的治疗,使75%的患者肿瘤明显缩小,这种状况持续了近一年的时间。6名晚期淋巴瘤患者10多年来一直处于完全临床缓解状态,CAT扫描或者身体检查都没有在患者体内发现肿瘤。赖威医生通过应用最新的诊断技术,在长期症状缓解的患者身上发现了少量流动的淋巴瘤细胞;患者免受癌症困扰的原因在于,最初的抗体疗法刺激了人体免疫系统,使其产生反应。遗憾的是个性化癌症治疗法费用高昂不适合商业推广。最近IDEC公司的首席执行总裁威廉姆·拉斯泰特(Dr. William Rastetter)向我解释道:“(这种疗法的)医学价值很高,但不是一门划算的生意。”
然而尽管赖威医生的抗体疗法没有实用价值,却证实了一个原理。他有证据表明可以引导免疫系统识别肿瘤中的独特蛋白质,促使不治之症退化。因此20世纪90年代早期,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团队转向研发肿瘤疫苗,试图让癌症患者分泌出类似于小鼠体内的抗体。这是比较简单的技术但赖威医生已经证明了其临床上的有效性。
赖威的方法是:提取淋巴瘤患者的个体基因型的免疫蛋白球,即癌症的信号蛋白,然后利用它制造出疫苗。由于白血球能将肿瘤蛋白转换为能激活特异蛋白免疫反应的形态,所以赖威的操作步骤之一是将疫苗与患者的白血球样本混合。今年7月,10名癌细胞已大范围扩散的癌症患者经此程序注射疫苗,其中4名患者的肿瘤显著缩小,3名患者完全康复;且此方法无明显的副作用。
跟其他癌症专家一样,威廉姆·法尔对赖威的成功持有浓厚的兴趣,但是他知道不同类型的癌症对免疫系统抑制的反应不一,有强有弱。例如淋巴瘤可能对抗体和杀伤T细胞的攻击特别敏感。这一挑战使得更多的研究精力投入到如何激发免疫系统对抗至今仍十分棘手的癌症(即对免疫系统抑制反应较弱的癌症)上,例如结肠癌。所以当法尔向老朋友伊莱·基博尔(Dr.Eli Gilboa,曾是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治疗中心的研究员)求助研制个性化的肿瘤疫苗时,出于科学研究和私人情分,基博尔爽快答应。
基博尔医生当时在杜克大学,他是一位驰名全球的生物学家,搭建了癌症基因学与临床治疗沟通的桥梁。他在杜克大学的实验室已测验过一种旨在治疗多种类型肠癌的通用肿瘤疫苗。基博尔医生不清楚法尔结肠癌细胞内哪种信号蛋白能激活最有效的免疫反应,因此年初他致力于研究斯科普·赫斯顿早前准备的孵化细胞系,然后创造出一种疫苗,这种疫苗使法尔免疫系统中的变异蛋白在乳头试管中得以完全呈现。疫苗激活了法尔血液中的大量杀伤性T细胞,把结肠癌细胞与其混合后,T细胞将癌细胞消灭殆尽。
只有通过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的审批,个性化肿瘤疫苗才能用于患者治疗。与基博尔医生共事的凯姆·拉尔里医生(Dr.Kim Lyerly),为唯一的患者——威廉姆·法尔提交了医疗方案。在“同情协议”下,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通常会批准针对一个患者的单独治疗方案,法尔的情况就是如此。杜克大学的实验室冰箱里,有支疫苗上贴着“法尔”的名字,等待着给法尔注射。
抗癌疫苗:挑战和机遇并存
法尔深知,自己作为患者被格外优待的原因在于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广博的人脉。大多数的癌症患者不会选择量身定制的非传统疗法。但法尔仍期待有一天能普及癌症个性化治疗。他列举出自己必须应对的障碍:肿瘤细胞与生俱来的旺盛繁殖力与在实验室永久保存的难题;需要在试管和小动物身上进行大量试验,以筛选出可主动抑制肿瘤生长的混合抗体;为了描述癌症基因的特性和研发个体化疗法,需要诸如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治疗中心和杜克大学等机构的支持。
这些障碍不会轻易被克服。15年前,一家名为Biotherapeutics的公司成立,试图用一系列现有药物和免疫疗法对抗肿瘤,根据患者的病情选择相应的治疗方法,但均以失败告终,其原因不在于患者支付不起费用,而是疗效令人大失所望。当时,知识和技术匮乏、可用疗法选择不多:对促使癌症生长的基因突变了解甚少,在试管中试验的抗肿瘤疗法难以预测在患者身上临床试验的结果。此后抗癌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将会有更大的进步。
今后实验室评估疗效的方法将会改善:效率更快,结果更加准确。借助自动化技术,微芯片能在数分钟内提供基因序列和基因变异情况。而且高性能电脑生成的肿瘤蛋白三维结构框架能加速新型抗癌药物和肿瘤疫苗的“理性设计”。虽然可预见的技术发展会加快抗癌研究的进程,但仍然会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费用高、人力需求大。法尔医生评论道:“如同人们花钱储存精子一样,也许有一天,有钱人会花钱储存他们的癌细胞,以便医生在诊断时进行研究。”
若利用培养出来的肿瘤组织作为研发新型抗癌药或新疫苗的模版取得了临床实验的成功,那么储存肿瘤组织用于研发的设想就能实现。即使现阶段未能取得成功,那些富有的癌症患者也会下定决心资助企业研发。如果疗效的确显著,难道就只能是富人的特权吗?到时就很难想象事态会如何发展:公众会进行强烈抗议,想要获得跟富人同等的医疗待遇。尤其是在美国这样一个高医疗保险费用的国家,保险公司该如何适应这一状况呢?
法尔很乐意让其他人参与思考这些问题。今年7月末,即法尔服用SPES11个月后,他做了一次CAT扫描,其结果显示肿瘤已经缩小,而且没有任何转移的迹象。法尔听到这个消息时当然很高兴,但是他并不满足于现在的研究成果。法尔知道若SPES内所含物质无法被鉴定,从而在其他由p53基因变异引起的病例中试验,他是无法单从他自身的案例中总结出SPES与结肠癌间的因果关系的。
SPES对法尔的效用暂时还是一桩轶事,一切还是老样子:考虑到之前法尔的癌症复发之快,他的肿瘤仍有可能重新生长。法尔说他已经决定要“尽可能尝试更多的草药和非传统疗法”并表示,如果癌症再次复发,他准备从事第二种个性化疗法的研究——肿瘤疫苗。他回想起暗无天日的治疗时光,在他的肝脏下方发现大量肿瘤时,法尔第一次觉得自己的存活几率陡然下降。
“我脑中闪过亲自研究自己肿瘤的想法,不过坦白说,我更看重生命和死亡。”法尔说道,他的语速迟缓让人听上去有些茫然。然后他又活跃起来,“当然脑海中有了这一想法后,我意识到这个想法真棒。” (全文完)
本文原文发表于1998年,文中的威廉姆·法尔医生已于2002年1月3日因结肠癌去世,享年6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