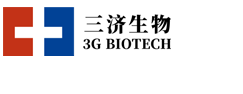你父母的悲惨童年或出色的冒险经历,都可能通过改变大脑里基因的表观遗传学信息而遗传给你,从而改变你的个性,赋予你或焦虑或达观的性格特征。
达尔文和弗洛伊德走进一家酒吧,正好有两只酗酒的老鼠——老鼠母亲和她的儿子——坐在酒吧凳子上,正在用两个小杯喝着杜松子酒。
母鼠抬起头看了看,说道:“嘿,两位天才!请你们告诉我,我儿子怎么变成这副酗酒德行的?”
“遗传不好。”达尔文说。
“家教不好。”弗洛伊德说。
家族的诅咒
一百多年来,对于个体以及不同代际之间的习惯的发展与继承,达尔文和弗洛伊德的观点——天生的还是后天养成的,生物学因素还是心理学原因——提供了两种相反的解释。
时间到了1992年。追随着弗洛伊德和达尔文的脚步,两位年轻的科学家的确走进了一间酒吧。喝了点啤酒之后,等他们走出酒吧的时候,对于人生经历——不仅包括你自己的人生经历,还包括你父辈的,祖辈的,等等——怎样直接影响你的基因,他们提出了一种新的革命性的观点。
这个酒吧位于马德里,当时西班牙最为历史悠久的神经生物学研究中心——卡哈尔研究所(Cajal Institute)正在那里举办国际学术大会。摩西· 西夫(Moshe Szyf)来自位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是一位分子生物学家和遗传学家,但他从未研究过心理学或神经生物学。他之所以参会,是因为一位同事说服他,说这可能给他的研究工作带来一些实际应用。同样地,迈克尔·米尼(Michael Meaney)也是被同一位同事说服而参会,这位同事认为,米尼的母性动物模型的疏漏之处,也许只有西夫能够察觉到。
“那是一间街头角落里的酒吧,比萨是其特色。”米尼说,“摩西是犹太人,只吃犹太教教义规定的食物。啤酒是一种犹太食品,摩西可以在任何地方喝啤酒。而我是个爱喝酒的爱尔兰人,所以我们很合得来。”
两人对遗传学研究的前沿热点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研究人员已经知道在每个细胞的细胞核内紧密缠绕的DNA长链需要一些额外的信息,以精确地告知它们哪些基因需要转录,是分化成一个心脏细胞,一个肝脏细胞,还是一个脑细胞。
这样的信息元件之一是甲基,一种常见的有机分子结构的组成成分。甲基的工作机制像是一本菜谱中的占位符,它们附着在每个细胞内的DNA上挑选所喜欢的“菜”,即基因,基因的主要功能是合成细胞中某一特定的蛋白质。因为甲基附着在基因表面,可以从双链DNA上分离下来,因此这一研究领域被称为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s)。
起初人们认为,这些表观遗传学的变化只是在胎儿发育过程中才会发生。然而一项开拓性的研究成果显示,这些小分子可以添加到成人的DNA中,开启导致癌症的细胞变化的级联反应。有时候甲基附着到DNA是由于饮食习惯的改变,有时候好像是由于接触某些化学物质。西夫的研究证明,在动物中用药物纠正某些表观遗传改变,能够治愈特定的癌症。
遗传学家惊讶地发现,表观遗传学改变能够从父母传给孩子,并一代一代地往下传递。杜克大学的兰迪·杰托(Randy Jirtle)的一项研究表明,用富含甲基的食物饲养雌性老鼠,其子代皮毛的颜色会发生永久性的改变。DNA本身没有任何改变,仅仅是增加或者减少了甲基,像是一个基因发生了突变一样。
现在,在位于马德里的这间酒吧里,西夫和米尼提出一个看似不可能但影响深远的假说:如果食物和化学药品可以导致表观遗传的改变,那么特定的经历,例如童年时疏于照顾、滥用药物或者是其他严重的挫折,是否也能引发大脑神经元里的DNA的表观遗传的改变? 原来,这个问题是行为表观遗传学(behavioral epigenetics)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基础问题。该领域充满活力,已经催生出了许多研究成果,并且对恢复大脑健康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新疗法。
按照行为表观遗传学的新观点,我们自身的过去,或者是我们较近祖先过去的创伤经历,都能够在我们的DNA上留下分子疤痕。其曾祖父曾在东欧犹太人村遭到追捕的犹太人;祖父母曾经历“文革”迫害的中国人;来自非洲,并且其父母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年轻的移民;每个民族中伴着酗酒或吸毒的父母成长起来的成年人;??都携带着这种疤痕,不仅仅是在记忆里。我们的经历,以及我们前辈的经历从未消失,即使它们已经被遗忘,它们实际上也已成了我们自身的一部分,一个由分子基团坚守的遗传学骨架。DNA还是一样的,但是心理和行为倾向被继承了下来。可能你所能继承的,不仅是你祖母的圆圆的膝盖,还有她在新生儿时由于缺乏关爱而引起的抑郁症倾向。
或者情况相反。如果你的奶奶被无微不至的父母抚养,她所感受到的父母的爱与支持,或许你此生仍能暗自享受。行为表观遗传学发挥作用的机制不仅是负面的和软弱的,也包括正面的和有力的。即使你不幸从命运悲苦的祖父母那里继承了遗传物质,只要用新的药物疗法进行治疗,你可以重新获得的不仅是情绪,而且还有表观遗传变化。一直以来,基因组都被称为生命的蓝图,而表观基因组就是生命的神奇画板:努力地改变它,你就能将家族的诅咒消除干净。
魔法遗传学
在推动一场生物学革命20年后,米尼坐在一个宽大的胡桃木办公桌后面。他的办公室在道格拉斯研究所四楼的一个角落里,该研究所是麦吉尔大学附属心理健康中心,从办公室前的落地窗户向外望去,一月份风暴带来的雪已经堆积了半英尺厚。米尼长着菱角分明的容貌和蓬乱斑白的头发,他办公室的地板上精心摆放着不同大小的氦气球,在祝贺米尼“60岁生日快乐”。
“一直以来,我对于为何每个人不同于彼此很感兴趣。”他说:“我们做事的方式,我们的行为方式都不同,有些人比较乐观,有些人是悲观的。是什么引起了这种变化?”
米尼探索个体差异的问题,是通过研究母鼠的抚养习惯是如何改变它们子代的一生来进行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人做实验,将出生后三周内的鼠崽每天进行5~15分钟处理,将其放至母鼠的身边。他们发现,与未经处理的个体相比,这些个体长大后性情更温和,对环境压力有更强的耐受性。米尼等人认为,人搬动鼠崽并不能为其带来直接的好处,然而,这种处理能使母鼠更多地舔舐幼崽并为其理毛,并且促使母鼠腾出更多的空间给鼠崽,让鼠崽在它身下吃奶。
在1997年发表于《科学》杂志的那篇有重大意义的论文中,米尼证明幼鼠接受舔舐和理毛行为的数量的自然变化,与皮质酮等应激激素在成年中的表达情况有直接的关系。幼鼠被舔舐得越多,长大后应激激素水平就越低。母鼠的舔舐行为与遗传学的控制开关二者之间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那篇论文中没能解释这二者是如何产生关联的。
“那时候我们竭力想要鉴定出母亲的照顾对特定基因的影响,”米尼说,“但是表观遗传学是我不熟悉的研究领域。”
然后他遇到了西夫。
后天的遗产
“我原本想要当一名牙医。”西夫笑着说。他苗条,苍白还有点秃顶,坐在位于他繁忙实验室后面的小办公室里。办公室很简朴,里面放了一张大大的图片,是一个子宫里孕育着两个胚胎的照片。
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需要撰写论文以申请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牙医专业的博士学位,西夫与一位名为阿龙·拉辛(Aharon Razin)的年轻的生物化学教授熟识。拉辛最近因为在一个少有人涉足的领域有重要发现而引起了轰动,他的研究首次证明,基因的行为可以被甲基所调控。对于这一领域,西夫几乎一无所知,不过他需要一位论文的导师,而拉辛就在那里。后来西夫才发现自己已置身于表观遗传学这一最热门的新领域的前沿,再也没有回头。
在拉辛等人探索这一领域之前,有关细胞中基因如何开始转录的基本故事情节紧凑而简单——DNA是主要的遗传密码,位于每个细胞的细胞核内;RNA转录遗传密码,合成细胞所需要的任何蛋白质。然而,拉辛的一些同事证明甲基能够附着在胞嘧啶上,胞嘧啶是DNA 和RNA的碱基组成成分之一。
拉辛与其同事霍华德·斯达(Howard Cedar)合作,证明这种附着不是短暂的行为,更不是毫无意义的事情。甲基像是与DNA永久地结婚了,哪怕是DNA复制到了第100代子代也会带着它。正如任何美满的婚姻,甲基的附着也显着地改变了它们所嫁的基因的行为,它们抑制基因的转录,就像是一个妒妇。拉辛和斯达的研究证明,当甲基缠绕在一种名叫组蛋白(位于细胞核内)的分子外面时,能收紧DNA链。DNA链收得越紧,基因产生蛋白质就越困难。
思索一下这意味着什么:DNA遗传密码本身并没有发生突变,甲基的附着导致了基因功能的长期、可遗传的改变。另外还有一种分子,被称为乙酰基,人们发现它起着相反的作用,它使DNA分子从组蛋白聚体上解开,从而使某一基因更容易转录为RNA。
西夫到达麦吉尔大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此时,他已经成为表观遗传学方面的专家。但是在遇到米尼之前,他从未听任何人说过表观遗传变化能在大脑里出现——仅仅是由于母亲的关爱。
“起初它听起来就像巫术。”西夫承认:“对一个分子生物学家来说,没有明确的分子途径的事情听起来都不是严谨的科学,但是我们交流的时间越长,我就越意识到母亲的关爱很可能的确能够导致DNA甲基化。这听起来有点疯狂,因此迈克尔和我决定用实验来探个究竟。”
他们最终做了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实验。在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协助下,他们首先选择非常关爱幼鼠的或者是特别不关心幼鼠的大鼠母亲。一旦幼鼠长至成年,这个团队就检查它的海马区——大脑中调节压力反应所必需的区域。在不关心幼鼠的大鼠母亲的孩子中,他们发现,负责生产肾上腺皮质激素受体的基因高度甲基化,这一激素能调控应激激素的敏感性;而在那些尽职尽责的妈妈的孩子中,肾上腺皮质激素受体基因很少被甲基化。
甲基化几乎总是把事情搞糟。与糟糕的养育相关的甲基化,阻止了正常数量的肾上腺皮质激素受体在幼鼠的脑海马中转录。由于缺乏充足的肾上腺皮质激素受体,这些幼鼠长大后就变得神经衰弱。
为了证明这种影响仅仅是由于母亲的行为,而非其基因引起,米尼和同事们又进行了第二个实验。他们把不关爱孩子的大鼠母亲所生育的幼鼠交给非常关爱子女的大鼠母亲,而把关爱子女的大鼠母亲的孩子交给没有责任心的大鼠母亲喂养。正如他们所预测的那样,由责任心强的母亲生育、而由忽视孩子的大鼠母亲养育的个体在长大以后,它们大脑海马区的肾上腺皮质激素受体水平较低,并且容易行为冲动。同样地,坏母亲生、好母亲养的个体长大后性情温和,比较勇敢,并且含有高水平的肾上腺皮质激素受体。
接下来的问题是,成年大鼠个体行为的改变真是由大脑中表观遗传的变化而引起的吗?为了证实这种因果关系,米尼和西夫又拿来由糟糕透了的母亲养育的幼鼠。他们往幼鼠大脑里注入了曲古霉素A(trichostatin A),一种可以去甲基化的药物。结果是,这些幼鼠从此直到长成成体,没有再次出现行为上的缺陷。
“想想往大脑里直接注入去甲基化药物就能发挥治疗作用,这听起来比较疯狂。”西夫说,“但事实的确是这样。就像是重新启动了一台电脑。”
当两人把研究成果写成一篇论文后,尽管看起来有充分的证据,一本顶级科学期刊的审稿人还是拒绝相信,因为在此之前他从未听说过一个母亲的行为能够导致表观遗传学特征改变的事儿。
“他当然没看到过了,”西夫说,“已经被证实的事情我们才懒得去报道呢。”
最终,《自然·神经科学》于2004年6月发表了他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母性行为引起表观遗传学重编程》。米尼和西夫证明了一些难以置信的事情,可以称其为后天遗传:虽然遗传密码没有变化,但仅仅是由于养育条件不同,幼鼠便获得了基因的附属产品——在基因的外面加了个甲基,由此改变了大脑的功能。
由鼠及人
米尼和西夫一起合作,已经发表了几十篇论文,找到了在大脑中活跃的许多其他基因表观遗传改变的证据。可能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由哥伦比亚大学副教授弗朗西丝·香槟(Frances Champagne)所领衔的一项研究,她的团队发现,在成长中受忽视的啮齿动物个体会导致大脑中雌激素受体基因甲基化。这样的幼鼠长大后,由于雌激素水平比较低,会导致它们对自己孩子的忽视,因此对后代的影响会继续下去。
在完成了大量动物试验之后,西夫和米尼已经进入行为表观遗传学研究的下一个关键步骤——对人类的研究。在200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他们对比了自杀身亡和由于其他原因意外身亡的人的大脑。他们发现,自杀者大脑的海马区(一个与记忆和应激反应有关的关键区域)基因过度甲基化。如果自杀者在孩童时期曾经滥用药物,那么他们大脑的甲基化程度会更高。
当然,从活人大脑中取样通常是很难的。但是检测人类的血液样本很常规,西夫于是就从血液中去寻找表观遗传的甲基化标志物。果然,到2011年,他报道了1958年出生的40名英国人的血液样本全基因分析研究结果。
在由孩子成长为中年的人生阶段,被调查的这40人都处于社会财富的两个极端——要么非常富有,要么非常贫穷。西夫总共分析了2万个基因的甲基化状态,其中,6167个基因因贫富程度的不同而有显着的变化。最令人吃惊的是,童年时家庭经济状况对基因甲基化的影响更明显,相当于成年后经济状况产生影响的2倍以上。
换句话说,时机很关键。在你只有两三岁时,你父母中了彩票或者破产变穷很容易使你大脑的表观遗传特征发生变化,影响你的感情倾向,其影响程度远甚于你在中年时经历这些后所产生的影响。
2012年,西夫和来自耶鲁大学的研究者发表了有关人类血液样本的另一项研究成果。他们比较了14个由亲生父母抚养的俄罗斯儿童和14个在俄罗斯孤儿院中成长的儿童,发现孤儿基因的甲基化数量明显增多。甲基化的基因中,有许多是在神经细胞通讯和大脑发育中起重要作用的基因。
“我们的研究表明,幼年与亲生父母分离的刺激对基因组功能具有长期的影响。这可能能够解释,为什么被收养的儿童在身心健康方面更加脆弱。”西夫的合作者、耶鲁儿童研究中心的心理学家艾琳娜·格雷戈里安(Elena Grigorenko)说:“对于被领养的孩子,也许应该给予他们更多关爱,以逆转他们在基因组调控方面的改变。”
下一步是什么
研究正日益深入。一个研究团队追踪到了老年人记忆力衰退与大脑神经元表观遗传改变的关系。另一项研究将创伤后应激障碍与编码神经营养因子基因的甲基化联系起来,该基因能够调控大脑中神经细胞的生长。
根据这些新的研究结果,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或平静或恐惧的倾向,以及我们学习或者遗忘的能力,都与大脑基因的表观遗传改变有关,那么是否可以用药物来冲洗掉不想要的甲基,恢复大脑原本的功能呢?
目前,大型制药公司和小型生物技术公司都在寻找促进学习和记忆的表观遗传学化合物。虽然至今尚没有人通过表观遗传介导的方法成功地对抑郁症、焦虑症和创伤后精神失调进行治疗,但是如果能找到这样的药物,将是一个重大飞跃。难点在于,如何能使这样的表观遗传药物只消除有害的标记,而留下有益的甚至很可能是必需的甲基化标记?
开发这样的药物还会牵涉伦理方面的问题。如果药物能够将历史留下的表观遗传特征擦拭干净,结果又会怎样?如果药物能够抹掉因战争、强奸,以及你祖先悲惨的童年而留在你大脑里的表观遗传碎片,你愿意服下它吗?